那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在一次战斗里,我负了伤,腿被子弹打穿了,红肿化脓,已经无法随同部队行军,便和另外十几个负伤的同志留下来,准备找个安全的地方养伤。
我们十几个伤员忍着伤痛、饥饿,在危机四伏的白区里走着,走着,到哪里去呢?到处是狼窝虎穴,到处是白色恐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红军手枪队同志身上。
当时活动在大别山的太湖区(今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的红二十八军,每离开一个地方就会留下几个便衣队同志,化了装做地下工作,宣传政策,组织群众,也负责收留伤员的工作,他们一定有办法安置我们。
希望,在鼓舞着我们,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天,终于在太阳落坡的时候找到了便衣队的同志,商量一阵后,他们决定把我们送到朱皮冲一位姓朱的老大爷家去住。
趁着黑泽,我们溜进了这座几十户人家的山村,山村背面是大山,山上长满了毛竹和松树,村后面山坡上有一栋小茅房,那就是朱大爷的家。
我们绕到房前,便衣队同志轻轻敲开了门,我们便不声不响地走了进去。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迎着我们,便衣队同志在老人的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介绍说:“这位就是朱大爷。”老大爷微笑着,向我们点头。
这一家五口人——除了老大爷老两口外,还有儿子、儿媳和一个十五六岁的闺女,他们可忙起来了,不一会儿,我们每个人都烫了脚,换下了湿袜湿鞋。
主人还特地炒了几个鸡蛋,让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老妈妈和儿媳闺女向我们问这问那,左一声同志,右一声同志地叫着,十分亲热。
老大爷却不言语,一会儿打烫脚水,一会儿拿铺草,忙得满脸是汗。
屋后高山腰里,有一片密密的毛竹林,竹林里有一个大石洞,地方很隐蔽,每天天不亮我们便进洞去,天黑了,方敢回屋里睡觉。几个重伤的同志,全靠老大爷和他的儿子背上背下。
我们的吃饭问题,由便衣队同志设法搞粮,在老大爷家煮熟了送上山来,每到吃饭的时候老大爷就来了,他假装成上山砍柴,腰里别着把柴刀,肩上扛着扁担,扁担上挂个竹篓,一般他先在外面咳嗽几声。
然后,朱大爷就分开毛竹向我们走来,来后,他坐下便给我们分吃的,常常是糊熟的芋头,间或一两次能带来大米饭,有时,便衣队同志搞到了西药和纱布,他便带着闺女来,一同给我们洗伤口,包扎。
我们天天跟老大爷打交道,他看来挺严肃,不苟言笑,老见他不声不响地进来,又不声不响地回去,但我们仍能从他慈祥的面容上,体会到老人给予我们的温暖。
有一次,他进洞来,嘴角上浮着笑容,我期待着他带来什么好消息,正想问他,只见他打开了竹篓,捧出一大缸热腾腾、香喷喷的猪肉来,原来是便衣队的同志替我们搞到了猪肉,老大爷为了我们能吃到一顿好饭而高兴哩。
又有一天中午,老大爷没送饭来,我们喝了些凉水,熬到傍晚,正盼着老大爷上来,却见他那闺女独自担了竹篓上来,当我们自己动手,打开竹篓,狼吞虎咽地吃饭时,闺女在一边,两眼望着我们,神情有点异样,问起她发生了什么事没有?
她终于说了出来,原来便衣队同志已经几天没送粮来了,为了不让我们饿肚子,老大爷把全家的口粮全烧给我们吃了,而老大爷一家,已经有好几天没吃饭了。听了她的话,我们再也咽不下饭去。
就这样隐藏了半个月左右,我们的行踪,终于被敌人探知了。
一天,从太湖出来敌人一个营,把朱皮冲包围起来,一批批进行搜山,这些家伙在我们隐藏的洞口前兜来兜去,还满山乱吆喝,可是洞里的我们,心里打定主意,决不投降,万一石洞被发现,就跟白军拼个你死我活,要是搜不到这个地点,就让敌人喊破喉咙,不去睬他。果然,敌人闹腾了一天,连个红军的影子也没捞到。
到天黑后,老大爷急急摸上山来,在他慈祥的脸上添了几分忧虑,敌人虽然返城去了,但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再来搜查,老大爷详细地向我们指点了山上更隐蔽的去处,并安慰重伤的同志说:“没关系,这阵风刮过去就没事了!”
然后老人担起他的竹篓,迈着沉重的步子下山去了。
入夜,听到朱皮冲村子里的狗吠声,隐隐传来的嘈杂的吵闹声,同志们整夜没有合上眼睛,黑夜的暗色,像是要从这里吞噬去什么似的,虽然我们为着自己的安全担心,但我们更为老大爷一家担心。
好容易待到天明,晨雾在洞口消失。“老大爷应该来了。”不知是谁说出了大家都在想着的事。
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老大爷并没有来。想到昨天夜里山下的喧闹,许多不好的想法涌上心头来,但是谁也不忍心讲出来,可能还有些什么事缠着身子,大爷不能来吧!
将近中午,终于有人上山来了,大家警觉地注视着,重伤的同志也扶着山石站起来,一阵抽噎的哭泣声,从竹林外面传来,越来越近,原来是小闺女来了。
她娇小的脸上像蒙了一层灰土,往日的娇羞欢笑一丝也没有了,头发散乱着,一双眼睛红肿得像两只枣,看见我们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瘫软地扑倒在地上,说不出话来,只是哭,哭得那样痛心,那样凄惨,我们劝慰她,过了好一阵,她才断断续续地说了半句话:“爸爸被白匪……”不用再问了,一切都明白了。
血冲上脸来,泪水模糊了眼睛,心好像要被撕碎,昨天老大爷还上山来看望我们,安慰我们,再三叮嘱这,叮嘱那,仅隔了一个夜晚,他竟遭了匪徒的毒手,再也不能见到他了。
直到后来便衣队同志找到我们,我们才详细地了解到老大爷牺牲的经过:那天夜里十一点的时候,有人敲老大爷的门:“开门,老头!我们是红军便衣队。”
大爷将门打开,拥进来一些打扮得像便衣队同志的人,但是,老大爷一眼就看穿了这些家伙的真面目,他们那鬼样子和说话的口气,就没有红军的味道。
“我们是红军主力,前几天我们留在你这里的伤员,多亏你照顾,现在交给我们吧!”
“留在这里的便衣队同志也请你找来吧!我们联系联系。”
老大爷摇了摇头说:“我们是老百姓,没见过你们红军同志。”这帮狼披羊皮的家伙又问了半天,老大爷什么也不说出来,只是摇头。
他们又问老妈妈,老妈妈也只有一句话:“我是个妇道人家,哪晓得这些事。”儿媳和闺女早躲避开了,敌人再也没有人好问。
鬼把戏玩不转了,便撕碎了脸皮,露出狰狞面目,厚颜无耻地说:“告诉你吧!老头子,我们是国军,早调查好了,你通红匪,今天不交出人来,剥你的皮。”说着,他们便七手八脚地把老大爷反绑了手吊起来,用手打,用脚踢,用鞭子抽,随你怎样折磨,老大爷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敌人闹了半夜,还是没有结果,最后把老大爷捆走了。
第二天早上,这伙敌人又来了,他们把全村百姓赶到一棵树下,树上吊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那正是朱大爷,已经奄奄一息了。
敌人用劈成四半的粗毛竹,猛力地往他身上抽打,打一下问一句:“交不交出红匪来?”
匪军还恐吓四周老百姓说:“看见没有,谁要是通红匪,就像他这样!”有人哭出声来,整个的天地变得凄惨阴沉。
老人被打得满身血糊,还是一字不说。敌人恼怒地发狂了,像野兽一样扑上去,竟挖下了老人的一双眼睛,鲜红的血顺着老人的脸淌了下来,滴在地上,朱大爷痛苦地呻吟着,但还是什么也不说。
乡亲们都哭了,为他求f青道:“他是好人呀!你们放了他吧!”敌人狞笑着。
突然,老大爷大声喊道:“你们是杀人放火的土匪,不说我没看到红军,就是看到了,也不会告诉你们!红军是打不垮的,他们就要回来杀死你们,为我报仇……”
话音未落,一把钢刀,猛地刺进老大爷的心口,乡亲们都用手蒙住了眼睛,不忍看这惨状,老大爷就这样为了我们红军伤员流尽了他最后的鲜血。
二十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今,每当我看到腿上那块痊愈的伤疤,就仿佛又看到老朱大爷,腰里别着把柴刀,肩上担着扁担,扁担上挂着个竹篓,分开毛竹向我走来……这是永远也不会忘掉的!
汪绍堂(1919——1984),安徽省六安市独山镇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党忠诚,作战勇敢。 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参与了鄂豫皖多次反围剿斗争,在最后一次反围剿斗争中奉命带领部队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未痊愈即找到并参加了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的红28军手枪团2中队,后任营指导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极其残酷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十个师近十万人对大别山区的"清剿"和地方反动势力实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怀着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希望,永保红旗不倒。
抗日战争时期任营长、水上大队长,渤海三分区十五团团长。汪绍堂同志是著名的神枪手。1942年8月任水上大队长期间,搜剿湖匪,打击日寇,保卫过往商船及水上交通安全,依靠老百姓有力的打击了日伪的有生力量。曾一次带领部队歼灭几百个日寇伪军,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使零星的根据地连成了片。汪绍堂同志坚持敌后抗战,率领部队开辟扩大了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时任33军296团团长,参加了苏北、泗州、昌潍等战斗,以及济南、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汪绍堂同志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上海战役在攻打嘉定的战斗中,他带领全团担任主攻任务,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英勇作战,身先士卒出色完成任务,荣获二等军功章。
上海解放后,任公安部队16师47团团长,后任上海警卫二团团长,担任上海警卫和陈毅市长的警卫任务,从战火纷飞的战场转入没有硝烟的阵地,在上海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拒腐蚀永不沾,继承和发扬了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1958年调任江苏盐城军分区参谋长。 汪绍堂同志戎马一生,出生入死,七次负伤,多次立功受奖,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55年授上校军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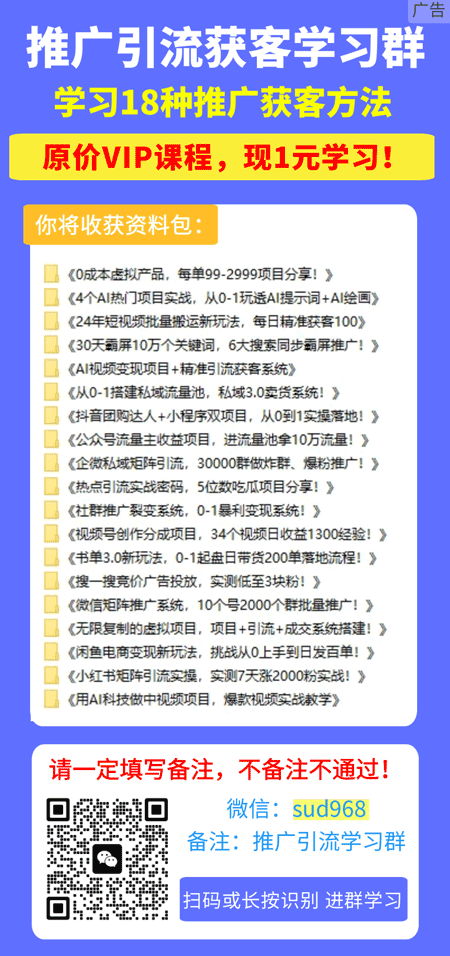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sumchina520@foxmail.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sumchina520@foxmail.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