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个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如今站在了《给力达人秀》的舞台上。
评委问我:「你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才艺?」
「我想为大家表演杀人。」
评委把嘴拱成O型,做出一个惊讶的表情,但马上又笑了笑,说:「哦,是魔术啊。」
我摇摇头:「不是魔术,是真的杀死……」我把眼睛眯起来,扫视了一下三位评委,继续说,「杀死一个人。」
观众席发出了嘘声。
但评委还是很镇定,问道:「是在这里吗?」
我点点头,把嘴角咧到两边,缓缓地从裤兜里拿出我准备好的尖刀……
1.
这是一个闷热的仲夏夜。
我正坐在宿舍看林潇雪演的《宫墙桃芳》。
室友宋鸿明走进宿舍,先把手里的篮球扔到角落,然后一边脱衣服,一边骂:「这鬼天气,真特么热。」
宋鸿明换了条短裤,光着膀子,拿着盆,要去洗澡,出门前,像往常一样,给我扔下一句:「张小欢,把我衣服洗了。」
我木然地坐在椅子上,想假装听不到,但手却缓缓把电脑合上,拿上盆子,把宋鸿明的球衣、短裤、内裤、袜子放到盆里,走出宿舍门,去了水房。
我故意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水流砸在宋鸿明的白袜上,把袜子上黑黄的污渍,冲刷得仿佛烤焦的蛋挞。
盆里的水满了,我关了水龙头,拿起宋鸿明的袜子,倒上洗衣粉,开始慢慢地搓洗。
一边洗,一边想起了我的妈妈。
在我七岁的时候,妈妈站在街上,和村主任王贵军吵架,后来王贵军就打了我的妈妈。
晚上,爸爸和妈妈一起去王贵军家,再回来是被人抬着的,满身都是血。
爸爸妈妈在床上哼哼了半个月,最后都死了。
法院说,王贵军没有动手,是他13岁的小儿子王宇超用棒子打的,判了3年少管所管教。
「张小欢,你怎么还在这儿呢?」我正想着,一个急切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侧回头看去,是同班的杨树枫。
没等我问,他拉着我就走,说道:「你干啥来了,咋惹到机电系的瘦猴了?他正领着一帮人在楼下找你呢。」
杨树枫说起『瘦猴』,我想起今天食堂里遇到的一个瘦干瘦干的男生。
他踩了我一下脚,我往后退了退,他回头瞪了我一眼。
我眼睛比较大,有点儿甲亢,所以他觉得我也在瞪他。
所以他就问我:「你瞅啥?」
我没有说话,往左挪了挪,想离开。
他却伸出手,想推我一把。
我赶忙往旁边躲,他扑了个空,打了个趔趄,差点儿摔倒。
他回过身,抡着拳头,想打我。
这时候,一个女生拉住他,说:「算了,算了,咱们走吧。」
他朝我比了一下中指,就走了。
杨树枫拉着我,刚下到2楼,就又见到那个瘦干男生了。
他拉着一帮人,把我们俩堵到了楼道里。
2.
「张小欢是吧,知道为啥找你不?」瘦猴扬着下巴问。
杨树枫赶紧陪着笑脸凑上去,双手递出根烟说:「猴爷,肯定是误会了,我是小疯子,在腕儿爷手下混,这是我同学,农村来的,不懂事,但学习特好,您多包涵。」
瘦猴接过烟,杨树枫弯着腰给点上,瘦猴吸了一口,撇着嘴,说:「学习好?那咋跟爷一样上一中专?」
周围的人都一阵哄笑。
楼道里聚集了一群围观的同学,都是我们信息工程系的,他们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因为我是系里唯一认真学习的。
瘦猴清了清嗓子,朝前吐了口浓痰,落在我的裤子上。
我看见杨树枫的脸色僵了,好像一尊石膏像。
瘦猴朝杨树枫瞥了一眼,说:「这儿没你事儿,给爷滚远点儿。」
杨树枫点点头,退出了人群。
就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四周围都黑压压的,好像头顶盘旋着一群乌鸦。
「对不起。」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先道个歉。
他们又笑了,「嘿,猴爷,这哥们儿够带劲儿的,可以多玩会儿呀。」
瘦猴嘴咧得像个鸭子,左右看了看,吼了声:「带他到飞哥那儿玩儿会儿去。」
接着,我被他们推搡着下了楼,上了一辆面包车。
车子开到了郊区,这里一栋栋居民楼高耸入云,都是拆迁安置房,小区很干净,也很荒凉。
他们带我到了一处居民楼,里面乱糟糟的,各种零食袋子、饮料瓶子、烟头扔了满地。
一个满头黄毛的青年斜躺在沙发上,骨瘦如柴,脸色灰的像个死人。
「飞哥,给你带来个好玩意儿,瞧这小身板儿,跟个娘们儿似的。」瘦猴一进门就对那个黄毛青年说道。
飞哥把眼睛眯成一道缝,盯着我看了半刻,脸上浮起一丝笑意。
后来他们给我换上了一身女孩儿的衣服,小白蕾丝袖口衬衫,粉色花格裙子,白丝袜,然后开始了他们的游戏。
折腾到半夜,他们才放我走。
刚走出小区大门,就看到几条野狗,在垃圾堆那里,围着一条小博美耍。
这条小博美毛很干净,大概是走丢了。
我趴在地上,哇哇地吐了出来,全身都疼。
3.
这里离学校有十几公里,我手机开着导航往回走。
黑夜让我想起了父母死前『哼哼唧唧』的声音。
我的嘴角像被两条钩子挂着,上面拴着沉沉的石头。
沿着『宁远河』边走了很远,水面的波纹一直都像一只苍白的手在不断地向我招摇。
远远地,我能看到学校里那座二十层高的『琪美斯』楼,这座楼是由『琪美斯』丝袜集团捐助的。
楼顶此时正盘旋着一团团的乌云,记得去年有个女生就是从这座楼上跳下去的。
在我和楼之间的位置,『希望桥』横跨在『宁远河』之上。
桥上的鹰架挂着五彩斑斓的灯条,如同彩虹横架在夜空。
我走近了些,桥底下的桥洞里,有个黑影在晃动。
是住在桥洞里的流浪汉,他像是在跳舞,扭动着肮脏笨拙的身子。
没有音乐伴奏,只有冷风的呼啸。
我停下脚步,站在河边,看他跳舞。
他的舞步很欢快,手里抱着一个脏兮兮的洋娃娃,不时地用他胡子拉碴的嘴去吻她。
他闭着眼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十分陶醉。
我嘴角的钩子断了,紧绷的面部肌肉松弛开。
我如同神经病一样在夜里狂笑起来。
笑声惊动了那个流浪汉,他睁开眼,循着声音朝我望过来。
发现了我,于是朝我招了招手,让我下来。
他的桌子上摆着半瓶白酒,一袋子花生米,几根朽了的辣椒。
「学生?」
我点点头。
「失恋了?」
我摇摇头。
「哈哈,喝吧。」他把酒瓶递给我。
酒的味道很冲,像两根筷子突然插入鼻孔。
爸爸也爱喝酒,每次都用筷子沾一点儿往我嘴里塞,我被辣得喘大气,他就会哈哈大笑,好像在耍猴一样。
我接过酒瓶,『吨吨吨』灌到嘴里。
我醉倒前,好像听那个流浪汉说了一句:「浪费!」
4.
我再次醒来,还是黑夜,是被桥底的夜风吹醒的。
周围黑黢黢的仿佛煤窑,一点红火星子在黑暗里慵懒地呼吸。
从大概的轮廓能看出,是流浪汉坐在那儿抽烟。
他身子佝偻,团在那里,像是一堆煤球。
我脑袋还是晕晕的,站起来,身上的棉被掉落,便觉得下身一阵凉意。
我的裤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脱了。
后面像是比从小区刚出来时更疼更肿了。
我意识到了是什么情况,指着流浪汉,生气地问道:「你……你……你……」
但我终于还是一个字也蹦不出。
「啊……啊……」,吼了两声,然后又坐倒在地,一边穿裤子,一边哭。
流浪汉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烟头的红火星子有节奏地呼吸着。
我狠狠地瞪着流浪汉,心里在想:「连你这样垃圾一样的人,竟也来欺负我。你可是个流浪汉呀,就是把你杀了,都没人给你报案。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就跟垃圾堆里的蛆没什么区别。是呀,你干嘛活着呀。」
我穿好裤子,从地上拾起一块馒头大的鹅卵石,一步一步靠近流浪汉。
流浪汉还是坐在那儿抽烟,脏兮兮的洋娃娃躺在他脚边,一双眼睛有铜铃那么大,像是在看我,又像是在看流浪汉。
我走到流浪汉身边,猛地举起鹅卵石,狠狠砸在他的脑袋上。
流浪汉向前倒下,脸怼在洋娃娃的胸脯上,身子蜷缩地像一条狗,鲜血从他的额角流出来,把洋娃娃的花衣服染成了鲜红。
「垃圾!垃圾!垃圾!」我冲着流浪汉,骂出了声。
流浪汉倒在地上,喘着粗气,嘴里发出『嗷嗷』的声音,像一头发情的母牛。
我不停地用石头砸向他的脑袋,脑浆流在地上,被血染成红色,里面混杂着细碎的头骨片。
天快亮了,太阳从远山后面透出一缕晨光,把桥洞里照得彤红,映在河面上却是黄色的,天很蓝。
5.
我回到宿舍,大概是六点。
「你特么不能小点儿声!」宋鸿明被我吵醒了,在被窝里骂骂咧咧。
我不理他,径直往我床边走。
忽然脑袋就被踢了一下。
我回过头,宋鸿明坐起来 ,他用光脚丫朝我脸上又踹了一脚说,「贱×,你昨儿上哪儿疯去了?尼玛把爷衣服搁水房不管啦?找人开房去了?」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过身,登着梯子爬上床去,盖好被子,闭上眼。
但我睡不着,可能是害怕,心里想:「一个流浪汉死了,警察应该不会管吧。」
宋鸿明怒了,骂道:「你特么是不是哑巴了?」
我心如死灰,躺在床上,一下子也不想动,心道:「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宋鸿明真的到我床上来了,骑在我身上,扇我耳光,扇一下,就骂我一声『贱×』。
我像头死猪那样躺在那儿。
宋鸿明打累了,手指颤抖着指着我的鼻子说:「行,你行。」然后走了。
第二天,我发高烧了,全身软得像死了一样,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
中午,宋鸿明回来了,我听到他像是把什么东西放在我的桌子上,然后就走了。
我渴了,下床喝水,看到桌上放着一份盒饭,还有几袋感冒冲剂。
我吃过饭,喝了药,感觉好些了,便又躺回床上睡着。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每天宋鸿明会给我带饭,但我们没有再说过话。
这一天,我坐在电脑前看《宫墙桃芳》,宋鸿明进来了,问:「你好了?」
我回过头,看见他是笑着的。
他说:「走,一起吃个饭去。」
我们去了学校门口的沙县小吃。
「那天机电的瘦猴把你带走了?」
我点点头。
「他们怎么你了?」
我停下筷子,不说话。
「张小欢,你要把我当兄弟,你就跟我说,我给你报仇去。」
我略略沉默了一下,把那天的事情全告诉了他。
宋鸿明拳头紧握,咬着下嘴唇,说:「行,我知道了。」
说完,他放下筷子,起身到柜台付了账,便走了。
我一个人把剩下的饭菜打包起来,回了宿舍。
6.
我接到宋鸿明的电话,他让我去学校西侧的那栋废楼。
我到了楼底下时,宋鸿明朝我挥了挥手。
他穿着一件红色夹克,在灰白的楼面上,像姨妈巾上的一滴血。
我算好楼层,走了上去。
楼道里有很多大便,已经风干。
我来到宋鸿明在的房间里,角落里,瘦猴被扒光了,绑得像个粽子,全身红一片,紫一片,显然已经被打过了,一句话不说,看着我。
宋鸿明递给我一根棍子,说:「你想怎么弄他,去吧,别弄死就行。」
我接过棍子,站在瘦猴的面前。
瘦猴跪倒在地,不住地朝我磕头,喃喃地说:「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错了,我不敢了……」
宋鸿明猛地飞身过来,一脚揣在瘦猴脸上。
瘦猴向一边倒去,脑袋撞在墙上,鲜血从额角流下。
「你特么给爷跪好,谁让你瞎哔哔来。」
瘦猴全身颤抖,像一根蛆一样滚过来,又跪在我和宋鸿明面前。
宋鸿明一脚把瘦猴的脑袋踩在地上,看着我,扬了扬下巴,说:「小欢,你去拿棍子捅他后面。」
我看着瘦猴在那儿撅着,觉得很恶心。
我说:「算了,可以了。」
宋鸿明却像是怒了,瞪着我,骂道:「张小欢,你别特么跟个娘们儿似的,爷费这么大劲给你出气,你在这儿给爷说可以了?去,捅他。」
我还站在那儿,无动于衷。
宋鸿明夺下了我的棍子。
我背过身去,听到后面瘦猴凄惨地叫着。
宋鸿明却更兴奋了,骂道:「你特么知不知道,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今儿爷让你长长记性。」
身后,宋鸿明还在折磨着瘦猴,我蹲了下来。
我的脚边有一块砖头,中间部位,烧得漆黑。
我捡起砖头,站起身,走到宋鸿明身后。
宋鸿明用棍子打瘦猴,越打越兴奋,没有注意到我。
我举起砖头,猛地砸在宋鸿明的后脑勺上。
宋鸿明向前扑倒,压在瘦猴身上。
「我不是你的狗。」
不知道宋鸿明听见没,我看不见他的脸。
瘦猴听见了,嘴扁得像个茄子,『哇』得一声哭了出来。
「妈妈,我怕,妈妈,我害怕……」
瘦猴像个疯子一样喊着。
我俯下身子,猛地用石头又砸了一下宋鸿明。
宋鸿明的脑袋被我砸扁了,我听到了他头骨碎裂的声音。
脑浆从头骨的缝隙里流出来,流到瘦猴的嘴里。
7.
瘦猴的身体快速地抽动着,干呕着。
我照着瘦猴身体抽动的节奏,继续砸着宋鸿明的脑袋,又把宋鸿明的脑浆,涂了瘦猴满脸。
瘦猴翻白眼了,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喉咙里发出仿佛驴叫的声音,太阳穴的血管突了起来。
这声音让我想起了家乡,小的时候,家里也有一头小花驴。
爸爸把我放到小花驴上,带着我去镇上赶集。
镇上的面人很漂亮,有孙悟空,还有哪吒。
我想要一个,爸爸不给我买,我哭,爸爸就打我。
爸爸把我从小花驴上拽下来,扔在街上,用手打屁股。
我还哭,爸爸就用鞭子打。
后来我哭得没有泪了,喉咙里也发出像是驴叫的声音。
爸爸不打我了,给我买了一个孙悟空。
我拿着孙悟空,骑着小花驴,和爸爸回家了。
瘦猴的身体不动了,眼珠突起,像是快要掉出来了,眼角流着鲜血。
他不再呼吸了,张着嘴,像是一只刚刚被褪了毛的母鸡。
宋鸿明和瘦猴都死了,一个被我打死,一个被我吓死。
我不能回学校了,警察会抓我。
我又跑到『希望桥』的桥洞下,那个流浪汉的尸体还静静地蜷缩在地上。
果然是没有人在意一个流浪汉的死亡。
他的身体上爬满了老鼠,白色的虫子把他的身体咬出许多小孔,成为了它们孵卵的窝。
我从它的箱子里找了些能用的东西,旧衣服,旧碗旧盆,旧水壶……
我走了,成了一个流浪汉,逃回到我的老家,藏在老房子后面的山上。
从山上朝下看去,我家的老房子像个茅坑,院子里长满了杂草。
老房子旁边就是村主任王贵军家,他们家翻盖了新房,六层楼的别墅,白色的墙,红色的瓦。
我站在山上,脱下裤子,朝王贵军家尿尿。
但我射不远,只能尿到他们家屋后,于是我有个愿望,我要去王贵军家尿尿。
8.
这一天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王贵军家的墙上贴了许多喜字,鞭炮声震天响。
许多鞭炮节子飞溅到了我家老房子,我恨得不得了。
一辆奔驰车开到王贵军家门口,一个身穿笔挺西装的新郎官一直在门口等着。
我还能认出,那就是长大后的王宇超,他从奔驰车里抱出了新娘子。
新娘子穿着红色的婚纱,红色的丝袜,红色的高跟鞋。
王宇超很瘦,弓着腰,用手紧紧托着新娘子的屁股,有点儿吃力。
就这么病秧子一样的废物,当初是怎么杀死我爸妈的呢。
我不想看王宇超,我喜欢看新娘子,那是个漂亮的姑娘,嘴唇鲜红,脸蛋粉红。
自从杀了几个人以后,我越来越喜欢红色。
后来他们开始玩了,几个愣头青起着哄,把王宇超衣服扒光,只留下一条红内裤。
这家伙的皮肤真白,比女人的皮肤还白。
王宇超俯身趴在地上,新娘子骑上他,用手打他的屁股,他想狗一样在地上爬。
他们又把王宇超捆在他们家门口的电线杆上,新娘子用红色的鞭子抽打着王宇超。
王宇超像个女人一样扭动着他苗条纤细的身子,『啊、啊』地叫着。
他们热热闹闹地玩了一天,送走了客人。
我从别墅的灯光判断出,王贵军自己住在一楼,他老伴可能已经过世了,王宇超和新娘子住六楼。
我翻墙进到他们家别墅,从别墅后墙的钢筋梯爬到了别墅的天台。
又从天台阳光房的门,潜入到别墅六楼。
我听到六楼的卧室里,正在鬼哭狼嚎。
我不想现在就惊动他们,就在门口坐下了。
「小琴,我好像有点儿不行,要不你来上边吧?」
「你真没用,偏偏赶上洞房花烛夜你就不行了。」
「这不平时跟你玩的太嗨了么,有点儿肾虚。」
「哼,人家小说里的霸道总裁,每天晚上七八次都没问题。」
「那不是小说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行、行、行,我上去。」
接着,王宇超又开始『啊、啊』地叫着,像个女人。
「小琴,继续啊,我快好了,快、快……」
「来了,老公,我来了……」
他们都很兴奋,所以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进卧室,他们没有发现。
屋里只床头开着一个粉色的小夜灯,能照见王宇超的脸,他现在十分陶醉,把细嫩的天鹅颈妩媚地舒展开。
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脖子,我飞身过去,一刀刺进王宇超的颈动脉。
鲜血射了出来,喷得新娘子满脸都是。
没等新娘子喊出声,我把新娘子压在床上,捂住她的嘴。
「你没欺负过我,我不会杀你,但你不要说话。」
新娘子点点头,鲜血把她的眼睛也染红了。
「你坐好,不要动。」
我把枕巾团成一团,塞到新娘子的嘴里,又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紧紧地把她捆起来。
她就像一朵被暴风雨摧残的小花,无助地看着我。
我不再理她,一手推着王宇超的下巴,另一只手用刀把他的脑袋割下来,走出了卧室。
9.
我下到一楼,从厨房拿出一个盘子,放到餐厅的桌子上,把王宇超的头放在盘子上面。
然后站在餐桌上,朝王宇超的脑袋撒尿。
王贵军的卧室离餐厅不远,他听到响声,走了出来。
他看见我了,有些惊慌,回身就往卧室跑。
我把刀扔出去,扎到他的大腿上。
王贵军跌倒在地。
我走过去,拽住王贵军的头发,把他拖到餐桌前,提起来,让他端坐在椅子上。
他看见了王宇超的头颅,一耸肩,晕了过去。
我不想杀他,他说爸爸妈妈是王宇超杀的,不是他杀的。
王宇超认了罪,我也找不到别的证据,我没理由再杀王贵军。
但我想起来,王贵军和妈妈在十字街吵架时,说妈妈是婊子。
这个仇我得报,所以我站在餐桌上,脱下裤子,又朝王贵军的脑袋上尿尿。
王贵军的头顶没有头发,尿淋在上面,凝成一粒粒晶莹的小水珠,又顺着他硕大的额头流下来,有的流进了眼睛,有的流进了嘴里。
王贵军醒了,他还是惊慌的,他问我:「你……你是谁?」
我回答:「我是李素娥和张宝成的儿子张小欢,十年前,你说你13岁的儿子王宇超杀了我的父母,所以我今天来报仇了。」
「呜……」王贵军像个小孩子一样哭了,眼泪混杂着尿液从他的脸颊流下来。
「呜……,呜……,呜……」
王贵军的哭声好奇怪,像是蒸汽火车的鸣笛。
「你别哭了,我不杀你,因为不是你杀的我爸妈,但你侮辱我妈是婊子,我不太会骂人,所以就往你头上尿尿,表示侮辱,一码归一码,现在咱们扯平了。」
「你杀了我吧。」王贵军一边哭,一边说。
「我不杀你。」我回答。
「你杀了我吧,是我杀了你爸妈,我儿子他是无辜的,当时,我儿子是未成年人,不会判刑,所以我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打点了一圈,就让儿子顶罪了,不然我一定会被判死刑的。」
我穿好裤子,看着王贵军,他低着头,露出秃秃的头顶,周围长着一圈毛,像一个屁股。
10.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我问王贵军。
「我悔呀……儿子呀……爸爸害了你呀……」
「是不是生不如死?」
「你杀了我吧……我不该活呀……十年前就该死啦……」
我弯下腰,从他腿上拔下刀。
王贵军大概已经麻木了,血在流,但他没有喊疼。
我用两个指头捏着刀尖,把刀提溜在他的面前。
王贵军眼神空洞,像是在看着刀,又像是在看着我。
「这里有把刀,你用它自杀好吗?」
王贵军像个木偶一样点点头,然后缓缓地抬起手,握住了刀柄。
我把手松开,看着王贵军把刀尖对准了自己的喉咙。
刀尖刚刚刺入一点的时候,他的手停下了。
两行眼泪从他眼睛里流下来,头顶的一圈头发开始往下掉,脸色越来越灰白,长出许多皱纹。
王贵军在一瞬间,老了几十岁。
「十、九、八……」我开始为王贵军倒计时。
当我数到『一』的时候,王贵军把刀缓缓地插入,脑袋一歪,断了气。
我从王贵军家拿了几万现金,又开始了四处流亡的生活。
偶尔我会看看新闻。
关于王贵军一家被灭门的事情,警方的通报还没出来,但各路营销号、网络媒体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流量狂欢:
「震惊!多年鳏居的公公在儿子新婚之夜潜入洞房,割下儿子脑袋,强奸儿媳,然后自杀。」
「骇人听闻!儿子娶了自己的小情人,于是在洞房之夜杀死儿子,然后自杀。」
「当代凤仪亭惨案!王某军的仇人安排漂亮女子给他儿子当媳妇,该女子新婚之夜勾引公公,惹得父子俩互相残杀。」
报道越来越离谱,在他们眼里,人命不是人命,是流量。
我觉得,待在国内,迟早会被抓。
在电线杆上,看见了一个出国务工的小广告,我打过去电话。
联系到了蛇头,给了2万元好处费,他说可以走海路带我去泰国。
从曹妃甸码头上船,我们十几个人被塞进一个大集装箱。
集装箱里很黑、很闷、很热,大家都不敢说话,怕被发现,也是为了节省体力。
蛇头给准备了一些水和压缩饼干,我们要在里面待半个月左右。
吃、喝、拉、撒都在集装箱里面,很快就臭气熏天,集装箱上有一个小孔,大家可以轮流趴在上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在我旁边的是个年轻男子,头发很长,很瘦,皮肤很白,像个女孩子。
从上了船开始,他就不停地咳嗽。
七天过去了,这天他没再咳嗽,有人过来试了试他的鼻息,说他死了。
大家把他抬起来,扔到我们拉大便的地方。
船终于到泰国了,我们从集装箱里出来,那边的蛇头领着我们上了一辆大巴车。
车子开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蛇头让我们都下车。
这里有一处大院子,像是一个破烂的工厂,里面停着许多货车。
工厂门口有穿绿色军装的军人,手里都拿着枪。
蛇头领着我们进入厂区,给我们安排了宿舍。
吃过饭、洗过澡,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睡了一个好觉。
11.
「兄弟,你是咋就想来这里的?」
人们开始聊天了。
「唉,我赌博,输了几十万,就想着跑到国外,一是躲一躲,再来也想打打工,挣点儿钱,以后回去了还债。」
「我在老家砍了人,人家要我赔一百万,我哪有那么多钱呀,所以就出国了。」
「我是开车撞死个人,这不也跑了。」
也有人问我,我不想和他们多说,倒头睡下,面对着墙壁,不再理他们。
第二天,宿舍里进来一个寸头小青年,他把我和另外三个年轻男子叫了出去,送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
车开到城里,我们被安排到一个居民楼里住下。
一个红头发大妈进来说:「你们几个啊,就住在这里,按时服药,一个月以后,去做手术。」
「做什么手术?」同行的一个穿花格衬衫的男子问。
「去势手术啊,你们被卖到这里做人妖的。」
说完以后,红头发大妈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白色药瓶,上面写着『色谱龙』。
花格衬衫男子接过药瓶便直接扔到垃圾桶里,说:「我不吃,我是来打工的,开始也没说是要做人妖呀。」
红头发大妈瞪了他一眼,说:「你们这些长得清秀的,不做人妖可惜了,你给我把药捡回来。」
「我不捡。」花格衬衫扭了下身子,倔强地说。
红头发大妈看他一副娘娘腔的样子,毫无恶意地笑了,说道:「不想做啊,不要紧,我让阿龙过来劝劝你。」
说完,大妈就离开了。
不一会儿,一个梳着小辫子戴着墨镜的肌肉青年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根电棒,腰里别着一把匕首。
进来后,一句话不说,直接从床上把花格衬衫男子拽到地上,然后就用电棒电他。
花格衬衫男子双腿抽动着,往墙角逃,小辫子跟上去,像是戏弄一条小狗一样,一会儿用电棒捅他一下。
花格衬衫男子开始求饶了,小辫子男子说:「去把药捡回来,喝下去。」
花格衬衫连连说:「我吃,我吃,求你不要再电我了。」
说完以后,花格衬衫就要站起来,去捡药。
谁知他刚爬起来,小辫子便一脚把他踹倒,说:「谁让你起来了,你给我爬过去捡。」
花格衬衫不敢反抗,就真的爬过去了。
小辫子更得意了,双手叉着腰,看着花格衬衫。
我知道,机会来了,就趁现在,我猛地扑过去,用头顶到那小辫子的心窝,把他撞倒,夺下他的电棒,直接怼到他的心口,把电量开到最大。
小辫子一阵抽动,便晕了过去。
12.
我夺下小辫子的匕首和电棒,对另外三个男子说:「想不想跟我闯出去。」
他们木然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留在这里,就算是做了人妖,也会被他们玩弄、折磨,你们活不长的。」
一个高个子男子说:「行,我听你的,咱们一起出去。」
花格衬衫与另外一个爆炸头男子也点头表示同意了。
于是我们把床单撕开,把小辫子的双臂反绑起来,然后用水把他泼醒,用尖刀抵着他的脖子说:「带我们离开这里,不然我就杀了你。」
小辫子连连点头。
有阿龙做人质,我们顺利离开了那座居民楼,还开走了一辆面包车。
出了城,走到野外,我让爆炸头把车停下,我带着小辫子下了车,到路旁的沟里,一刀刺进他的颈动脉,又在来回划了几下,看着他的脑袋耷拉在那儿,确实死了,我才又上了车。
「你杀了他?」花格衬衫问。
「他该死。」我回答。
他们三人看我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了,不是感激,也不是愤恨,也许是害怕。
我让他们把车开到曼谷,然后我下了车,告诉他们,去中国的大使馆,想办法回国吧。
在曼谷,我当起了流浪汉,我喜欢去红灯区乞讨,那里的人都很大方。
我也喜欢坐在巷口,看着街上那些白花花的大腿,赏心悦目。
自从杀了人,我的血似乎变成冷的了,那里也很难再硬起来了。
但血似乎还没有全冷,有时也会饥渴。
我用讨来的钱去找人妖,让他们从后面来,并且从中得到满足。
我回忆起,瘦猴把我带到飞哥那里,让我穿女孩的衣服。
我发现,我的心境似乎也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我经常找的一个人妖,叫芳姐,有一次,我跟他说:「我也想像你们一样,不,还不一样,我像变得更彻底一些。」
芳姐说:「你个子适中,皮肤也好,面相也好,算是有天赋的。」
芳姐把我带到他的住处,开始教我化妆、服药,并且带着我去红灯区做生意,说等我攒够钱,就可以做变性手术了。
生意不忙时,我和芳姐在家里,拍一些小视频,发到抖音。
大家出于猎奇心理,以及对美色天然的亲近,纷纷给我们点赞。
「哇,简直比女孩子还漂亮。」
「果然是可爱的男孩子啊。」
「不行了,要把我掰弯了。」
三年后,我终于攒够钱了,做了手术,整了容,从黑市买了身份,名义上,我成了一个真正的泰国人,性别女。
有了新的身份,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想回到中国。
13.
因为之前攒着一些钱,所以我不再去红灯区做生意了,而是买了教材开始备考,我希望到中国去留学。
最后,我以国际生的身份,顺利申请入学到水木大学。
真是可笑,我一个中专生,仅仅是有了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就能轻松考入水木大学。
在学校里,我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他们只是认为,我是一个来自泰国的漂亮小姑娘。
但我似乎天生是一个不幸的人。
有一段时间,我开始频繁发烧、感冒。
我意识到,可能是那种病。
所以我去做了检查,结果出来了,HIV阳性。
我没有惊疑,也没有伤心,自从杀了人后,我的血是冷的。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在红灯区那么久,得这病也没什么意外的。
但我向往一个美丽的结局,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只静美。
对于现在的我,『杀人』似乎成了唯一可以称得上是艺术的东西。
暑假,我报名了《给力达人秀》,漂亮的外表,水木学霸的加成,让我顺利通过了海选,走上了舞台。
我告诉他们,我的才艺就是杀人。
我杀死了一个流浪汉。
又杀死了同学校的两个同学。
我回到村子,把我的杀父杀母仇人家灭门。
今天,我只杀一个人,就是我自己。
说完,我用尖刀割破我的颈动脉。
血液喷出很高,如礼花在空中绽放。
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觉得自己好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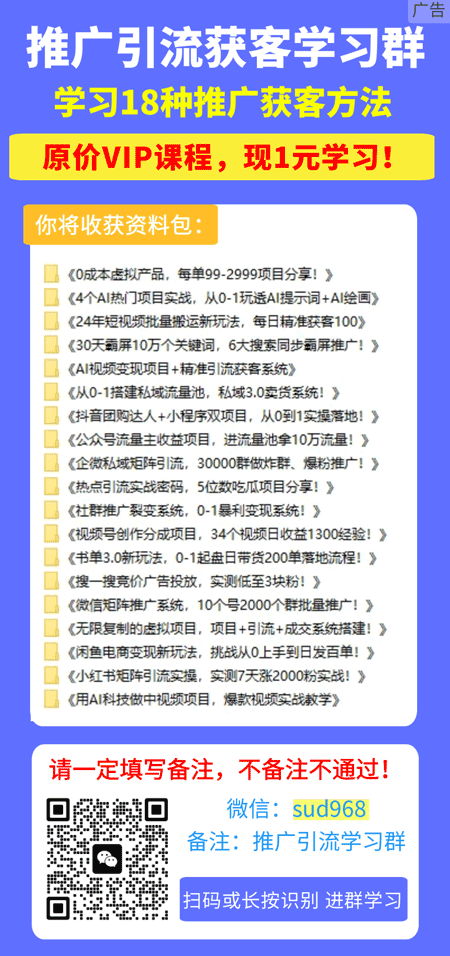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sumchina520@foxmail.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sumchina520@foxmail.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