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 :洪涛
作者:赵力
我们现在每天穿着白服工作,虽然不是医护人员,但我们很认真、更不敢掉以轻心。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略。
我还记得2009年冬天自己喝多了的样子。那是在一次工作晚餐上。也许是因为很少喝酒,在连续敬了几杯酒后,我晕得脑子都不清醒了。和我一起的同事说,我拉着当地卫生局领导的手,翻来覆去地念叨着那半句话,“你帮帮他……你帮帮他……”
就在端起第一杯酒前的几个小时里,我和黑龙江省红十字会、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走访了当地的几户艾滋感染者。当我们最后来到一位感染者家里时,不仅是我,同去的工作人员们也都震惊到无语了。
一拉开那扇小小的木头门,就能听到屋子里传出的呻吟声。那是一个才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他躺在炕上、蒙着被子,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声音不大地呻吟着。
炕的另一端,窗户用塑料布封死,上面结的全是霜。水泥地面,凸凹不平,像是一个个脚窝。屋里实在太冷了,我们在屋里说话,吐出一团团的哈气。因为是林区,小伙子的母亲去林子里采了点蘑菇,正给孩子煮汤,这或许是这个贫困家庭唯一能给孩子做的事情了。
小伙子的父母都已五十多岁,眼睛里透着无助。甚至连求我们帮忙,都不知道如何开口,只是局促地站在平房一角,尽可能地把空间留给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心都揪着。我实在忍不住了,晚饭的饭菜还没上桌,连着倒了几杯酒,敬当地卫生局领导,“这个小伙子真的太可怜,你帮帮他吧!”那位领导眼圈也红了,连着干了,“放心,放心!”
后来,红十字会和当地卫生局给小伙子想办法找了一车煤,还送了米面油。可小伙子病得很重。半个月后,听说他去世了。这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十八九岁这样美好的年纪,离开了世界。
哈尔滨的热线
生命中很多事情,似乎冥冥之中被安排着。2002年,我陪朋友去疾控中心检查。那时很多检测都只能在医院或疾控中心进行,比如查梅毒和性病,还有艾滋病。在疾控中心我见到了“哈尔滨同志健康热线”的负责人、一位疾控中心的医生。
1996年我大学毕业,到2002年时换过几份工作,一直处在比较好的岗位,做老板的助理、秘书或办公室主任。当时是一个网络不发达、群体社交清汤寡水的年代。医生和我聊了半个多小时,觉得我很热心,便让我去试一试当志愿者。
第一次去“哈尔滨同志热线”是深秋。那是一个五楼的民宅。一屋一厨,有一张“一头沉”的桌子、一个书架、一个不知道谁家淘汰的小沙发和茶几。最重要的是一部电话。每周二四六晚六点到九点,我们几个人会轮流来这里接热线。我们的编号里没有0号,没有1号,一开始挑头的就是2号。按照先后顺序,我是8号,后面有9号。
我们没有报酬,但特别喜欢这份工作。轮到接热线的时候,一下班我就赶过去。虽然每次会有十块钱补贴,但有次我加班出来晚了,打车过去单程就花了二十多块钱。
“同志热线”对当时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对于性取向、生活方式和艾滋病知识了解的渠道。从2002年到2005年,我接了几百个电话。当时人没有咨询1和0等话题的,打电话的朋友都是有着苦恼和困惑。夜里九点,接完热线的我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外加半小时步行回家。冬天很冷,但我穿得很多,走得很快,加上接热线很有成就感,一路上甚至会浑身冒汗。
当时我还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对这些并没有太多了解,如果问我,我会说工作需要加班。他们也理解。正是如此,让我在艾滋病这条路上,越走越深。
两个办公室
我从来都不是个聪明的人,可能我太老实了。从接“同志热线”开始,会有人打来电话,说想和我交朋友。可电话接线员有规定,不能和打来电话的人见面,更不能交朋友。那时也没有监听,我却老实地说,“对不起,我是八号接线员。你要是喜欢和我聊天,以后打来电话,可以问八号什么时候上班,但我们不能见面,我们只是通过电话咨询的工作关系。”
那时,我们既年轻,又很开心。我们很天真,很守规矩。我们也很认真。2005年,作为一个快三十岁的男人,总要找到一些支撑自己的力量。但心里多少有些失重。我的老板知道我接热线、做艾滋防治公益,就问,“你靠这个能养家糊口吗?”这话猛地道出了我心里不敢面对的问题。我骨子里觉得我们都是来自这个群体,很多朋友又感染了艾滋,我很想做这个工作。但做这个工作能养家糊口吗?
2007年,我回到哈尔滨,在一个比较大的房地产公司做老板秘书。那个时候,这个老板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套间:他在里面办公,平时关着门,足有一百平;我在外面,负责接待访客和一些行政上的事务,包括接待室足有二百平。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老板拍板说用我的时候,人力资源总监很担心,说看我就是心不在这份工作上的人。
也许总监看出了我的真实想法,所以转机出现得虽然很突然,但我几乎都没怎么考虑。当时省红十字会的一个处长约我在红十字会附近的一个面馆见面。这位很有魄力的女处长一边吃面一边向我介绍,荷兰红十字会资助中国红十字会在做一个国际项目,希望我到省红十字会做国际项目官员。
之前一直卡住我的“艾滋病工作没有固定收入”的难题迎刃而解。那时对我来说,做艾滋工作特别上瘾,不仅能体会到乐趣,还能吸引我一直做下去。
虽然省红十字会的名头很大,比亿万资产老板的公司好听得多,但却是一个穷衙门。这个国际项目的办公室大概十五平左右,有一个处长、一个员工,再加上我。办公室里除了三张桌椅,靠墙的全是办公柜,空间逼仄。
如果说以前我做艾滋病工作,完全是热情。那么到了红十字会,我才真正开始接触艾滋感染者。当时,我主要代表红十字会资助哈尔滨市内的多个小组办周末同伴教育培训班。培训班是分级培训,首先由红十字会将骨干集中起来培训,再由这些骨干担任同伴教育员,去给本小组内的更多进行培训。培训的形式也有很多,互动、游戏、脱敏,大家可以在培训上相互倾诉、聊天交流。我的工作除组织培训外,还要去各个培训班上督导,看是不是认真办。培训的效果越来越好,一开始只在哈尔滨开展,后来扩展到了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双鸭山……这些地方的小组至今依然活跃着。

参与红十字会项目时的洪涛
爱心家园
我虽然是做艾滋病工作的,但具体分工负责的却是艾滋感染者工作。那个时候,红十字会希望我能将在MSM项目中的经验扩展到艾滋感染者项目中。
红十字会和疾控合作,为艾滋感染者建立了“爱心家园”。这就像是一个基地,可以包容很多社会里难以接纳的人。当时艾滋项目的综合条件好一些,有单独的办公室。由于这是一个纯艾滋感染者组织,对我来说接触难度不是很大。我一开始去时,活动室每个月会组织两三次联谊和交流。可最初几次,来参加活动的感染者对我非常客气,从他们的眼神、语气中我能感觉到一种看不见的防备。
三次之后,他们忽然接受了我。他们说,看到我不介意和他们在同一个盘子里夹菜,用同一个杯子喝水,而且不是装出来的。感染者朋友们还告诉我,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和他们吃饭,甚至是一些医生可以过来上课、做培训,但到了吃饭的时候,会说自己有事、不参与了,或者说自己很忙,就走了。“好像一起吃饭就能把他们感染一样。”感染者朋友的语气里透着气愤和无奈。
在那个年代,对艾滋病的提防是很深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年感染者,一辈子没结婚,兄弟都歧视他。一次他去弟弟家取户口本,弟弟不让他进家门,而是用一个小篮子,把户口本从楼上放下来给他。有了爱心家园,逢年过节,我们就邀请他来吃饭。一次大年三十,他生病住院,我还和家里人一起去给他送了饭。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情况比较特殊。感染者都是因为太穷、不得不进行有偿献血而感染的。早些年,不仅经济不发达,医院对艾滋病的了解也很有限,越是小地方,歧视越严重,那些因手术和有偿献血感染的人,要经受身心的双重打击,其中很多人又是女性,生活起来更加艰难。于是我就去这里开展活动。几次之后,一个大姐拉住我的手说,“可想你来了!”只有我去了,她们才会有一个机会,可以在一起聚一聚,哪怕倒倒苦水。
其实,这位大姐生活也很苦。她家里是丈夫先感染,后来传染给她,她那个时候五十多岁了。有一次她路过姐姐家,口渴得厉害,就去讨一口水喝。她姐姐翻箱倒柜找出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的破碗,给她喝完之后,让她把碗也拿走。大姐和我讲这些的时候,眼里满是泪水。
这么多年,我做艾滋感染者的工作,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把苦都说出来,让大家听,然后相互安慰,彼此鼓励着更好地生活下去。

参与国际合作项目时的洪涛
穿起了白大褂
2012年,红十字会的国际合作项目结束,我也离开了,开始全职做黑龙江康同社区(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那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一年一搬家。一来是房东觉得我们是做艾滋病的,他们不喜欢。二来是我们最初也没什么钱,租房子都是挑便宜的。
几次后,我们也有了经验,会主动和房东讲,我们不是搞传销,是和红十字会、疾控中心一起,搞一个志愿者活动室。最初我们在“马丁基金会”的资助下,租了间五楼的民房。后来更换到一楼。虽然那些年不断地搬家,可这并不会影响每一个前来的感染者朋友都有一个“家”的感觉。
如果说我一开始接热线是出于热情,到红十字会做艾滋感染者工作是职业,那么我们从围绕着艾滋做宣传、再做实质性的检测,才是真正走上了艾滋干预的道路。
2011年,第一次接触到艾滋快速检测。在我看来,快速检测是医疗服务,虽然是第一次接触,但既不兴奋,也不害怕。脑子里想的就是学习到了一个新技能,可以给大家做服务。每一次做快速检测时,我考虑的都是扎的对不对,时间够不够,有没有做错?
第一次做出阳性,我自己很害怕,心里一遍遍问自己该怎么办?当然,我们现在通过快速检测的服务,很明确地知道能帮对方什么。可第一次面对自己检测出来的阳性,对方已经像天塌了一样,虽然后期还有确证检测,但我们的快检就是初筛,在他心里上仿佛有了一个判决。以前说做艾滋干预,基本上是敲锣打鼓喊口号做宣传,现在才是真的工作了,影响到了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对新检测发现的感染者,做的最多的就是陪伴和倾听。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感染了,坐在我这里,边哭边说,把面前一整包面巾纸全用没了。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陪在他身边。
还有一次,一位十七八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里快检初筛,发现感染。孩子很无助,告诉了妈妈。这位妈妈领着孩子过来,母子二人都哭了,一直问我该怎么办。这并不是个例。很多十八九岁的孩子在发现自己感染后,都很无助,只能告诉家长。家长也同样无助。母子二人在我办公室里一起哭的场景比较常见。我会耐心地讲给妈妈听,直到妈妈先平静下来,家长是孩子的主心骨,遇到家长带着孩子上门的情况,要多做家长的工作,对孩子有好处。

为服务对象提供检测咨询
2013年,在省市疾控中心的指导下,我们开展了哈尔滨市MSM人群哨点监测工作,并开始雇护士来办公室进行采静脉血检测。但并不是每个前来检测的人都会小心地把用过的棉签扔到垃圾桶里。于是,楼道里时常会有带血的棉签,邻居开始拨打市长热线举报,卫生监督所也来查我们。疾控中心得知后,也出面协调。但这样长期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在省市疾控中心的帮助下,我们搬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2014年,由社区医务人员来协助采血。
但好景不长,到了2015年,社区服务中心不让我们继续在那里工作了。主要是由于社区医务中心空间不大,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另外比较重要的原因是社区医务中心没有艾滋检测这项工作内容。
没想到的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志愿者领着艾滋感染者去传染病院治疗时,无意中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传染病医院很有兴趣和我们合作。后来省疾控和传染病院对接,医院给我们提供了独立的办公室,我们开始到传染病院工作。
现在,我们在传染病院形成一站式服务:动员检测、发现患者、在本院做确证、出报告,我们再接着和感染者联系、讲解、服务,再转给医生做抗病毒治疗。每年我们能检测出二百多位艾滋感染者。之前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三百多。现在每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一定比例的感染者是我们小组发现的。
我一直认为,艾滋预防是要走职业化道路,不能只靠热情。但是要让一批人可以认认真真全心全意做好工作,经费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年来,省市疾控中心一直支持我们、国家防艾基金办也在资助我们。2013年后,国际资金逐渐撤出中国,对于全国的社群组织来说都很困难,但是政府和疾控机构很重视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2014年,省疾控资助了我们一年,2015年国家成立了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基于我们的工作经验、人员能力、地方支持等原因,我们持续得到了基金的资助,也有了固定的工作人员。

2020年洪涛被聘为社会组织防艾基金第二届咨委会委员
我们现在每天穿着白大褂工作,虽然不是医护人员,但我们很认真、更不敢掉以轻心。虽然每天一遍遍地说着几乎一样的工作内容和做着同样的指导,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略。
但我们仍是一个民间机构,民政登记都没有。我从2014年开始跑注册的事,省民政、市民政都跑过,但一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业务主管部门,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实现民政登记。
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一直把艾滋病工作做下去。我的男朋友也非常支持我。我们在一起十三年了,是通过当年省红十字会活动认识的。我们俩现在基本上出柜了,过着老夫老妻的生活。他做饭既快又好。我却不会做饭,在家的工作就是刷碗。
如今,我也年近半百,和当年的大学同学们相比,也许他们赚到钱了,但是我觉得自己过得挺有意义的,每天可以在生活中能帮助很多人。我想这种成就感是他们没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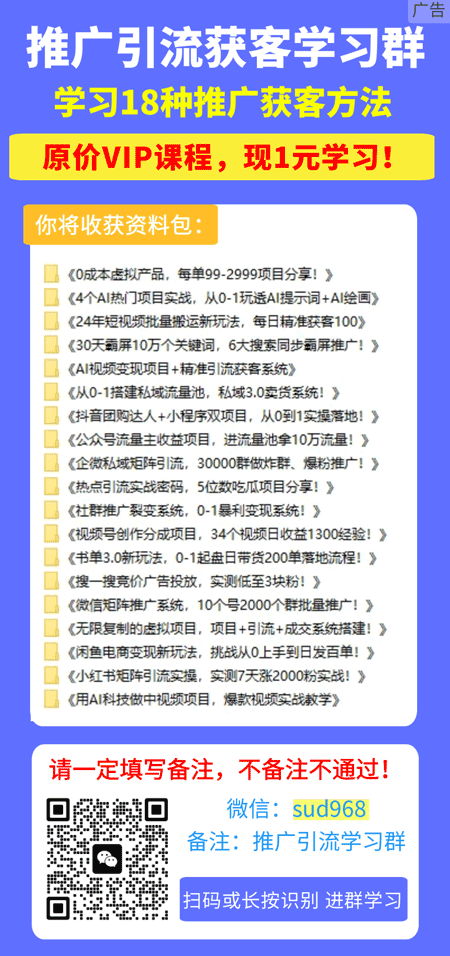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sumchina520@foxmail.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sumchina520@foxmail.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