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列写了200多天,今天到这里算画上一个句号。在最后,还是有几点需要特别说明。
首先,还是要再次强调早期党员入党时间的认定问题。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有涉及。本来,我是准备写到中共二大召开时所代表的195名党员的,但是真正查找资料动手写的时候却发现,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如果有的党员的入党时间只是在相关资料中笼统地记载为1922年入党,但到底是1922年几月份入党则语焉不详,所以,我就把所能找到的所有在1922年底前入党的党员都写进来了,他们中除了有最早的中共第一批和第二批党员外,有的是中共的第三甚至第四批党员,这样一来,这一个系列中介绍的党员就大大超出195人了。
认定早期党员还有一条标准也让我很是纠结,那就是有的人实际上是创党时期的参与人,但当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而是几年后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如我在这个系列中提到的吴玉章、杨闇公以及陈家安都是这种情况,特别是陈家安,他本来应当成为一大正式代表的,但阴错阳差地错过了一大。这样的人物还有不少,我在这里都没有写。但在最后还是有必要交代一下,比如彭湃,党史界公认他是1924年入党,但实际上他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由施存统介绍参加了中共日本早期组织的活动,回国后又与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谭平山接上了关系,从理论上说,他应当是创党人物之一,与他一起参加中共日本早期组织的林孔昭也是如此。再比如陈毅、邓小平等人,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已经参与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只不过那时候共青团和共产党经常是一道出现,旅欧的“少共”今天都被认定为共青团组织,事实上他们从事的活动也属于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而有的人入党时间存在争议,比如广东的郭瘦真等人,我在这里也没有把他们列入。
还有一些人,也曾经参与过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但后来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了,比如国民党的戴季陶、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等。此外,还有帮助共产党成立的共产国际人员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对于这些人,我也没有单独为他们写小传。
第二,党史上的人物有时写起来不好把握。有一些史料,特别是对党史上“盖棺论定”人物的一些史料是不能写出来的。比如,对邓中夏和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一些“左”的做法及其危害,即使是我从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找到的史料,写出来后平台审核也无法通过。因此,在这个系列中就缺少了夏曦的小传。
第三,早期党员中那些烈士的表现。受影视作品影响,我们一般都会以为烈士们都是受尽酷刑,走上刑场高呼口号,但实际上也不尽然。有一些人并没有受刑,被害时也没有喊口号,比如杨开慧、瞿秋白都没有受刑,杨开慧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坐在黄包车里一直沉默不语,直到牺牲。但这些都无损烈士们的英雄形象。
顺便说一句,在那个时候,多数死囚在去刑场的路上都要喊几句,这是从古代留下来的一个传统,据说喊上几句诸如“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话,死后会早日“托生”。一般在“出红差”(即处决人犯)前,狱卒会事先叮嘱死囚要“喊上几句”。而且那时处决人犯还沿袭封建时代的传统,路上的所有商铺都会关门,只有一家饭馆会在路边为死囚摆上酒肉(这个场面我曾经听老人亲口讲过他们见过的情形),为犯人“送行”,官方对死囚的呼喊乃至咒骂都以“死者为大”的传统,任由他们呼喊。只是到了国民党杀“政治犯”时,这种情况才出现了变化。因为国民党发现,很多政治犯在最后时刻会向周围的人演讲。这令国民党当局相当惊恐,所以才有了对向警予在口中塞满石块然后用皮带把她的嘴勒出血来,以阻止她讲话的残暴做法。
第四,写我们党的早期历史,特别是深入到史料中了解细节,会使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左”给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比如当年的“打AB团”“抓改组派”“肃反”等活动,让很多同志被枉杀,教训极为惨痛,这才有了沈泽民到临终时幡然悔悟,诚恳地向党认错,并表示要“从头做起”。至于王明搞的那一套,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就更大了。想到这些,我们会更深刻地体会小平同志的那句名言:“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整风就显得尤其必要了。实际上,共产党比国民党高出一筹的东西正是在于随时纠正偏差,强化思想建党,读党史时,对这一点体会尤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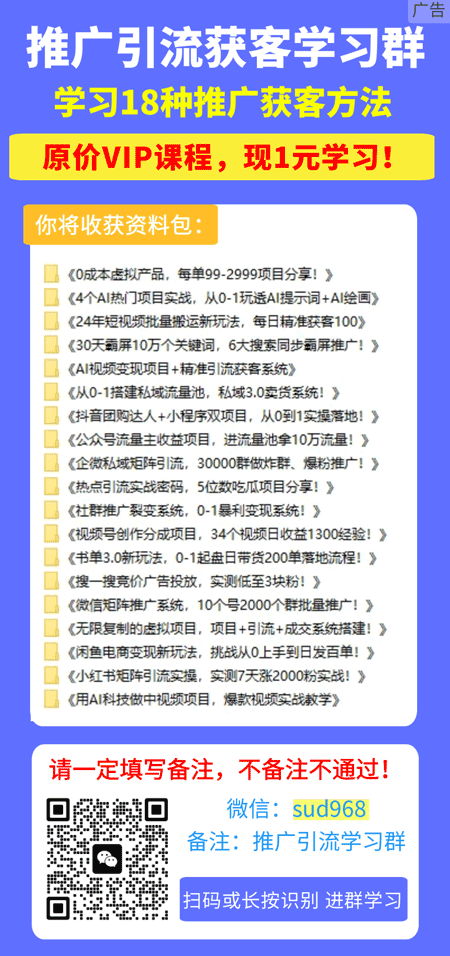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sumchina520@foxmail.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sumchina520@foxmail.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